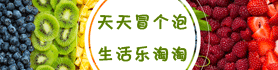我七岁的时候就开始一边上学一边放牛。那时,放一头牛一天有两分工分,放牛所得的工分值已足够我的口粮钱,父母为我能自己养活自己而高兴。
我放的牛是从邻村新买来的,和我一样,还是个“小孩子”。它和我在一起的时候,就像我要纠缠妈妈一样,用头从下向上往我身上撞个不停,像按摩似的,撞得我心里甜甜的,痒痒的,直到我把牛绳一摔,假装发火了,它才圆睁着两只铜钱一样大的眼睛,憨憨地看着我。它一身黑中透黄的牛毛油光发亮,牛角还没有长出来,牛角跟两丛黑毛好像是谁把它梳过一样往上翘着,颈部上方的肩头隆起一个圆圆的大肉墩,显得异常雄壮威武。
它来到新家的第一天,我就把它关进牛栏,开始它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,两眼傻傻地看我。当它知道已不自由了,就左三圈,右三圈,不停地在牛栏里转圈子。我关好了牛栏门,对它说:“明天见”,就回家了。想不到第二天早上去放牛时,早已牛走栏空,不辞而别了。我们只好全家都去寻找,但找了几个钟头,也没有见到踪影,心想:找回来非狠狠揍它一顿不可。直到中午,有人告诉我,它回“娘家”了。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,它和它的伙伴们三三两两在草地上悠然地吃着青草,看到我们走过去,好像并不认识,我们要去牵它了,它才走到它妈妈身边,用头不停撞它妈妈,它妈妈对它也像宝贝似的,用舌头不停地舔它前额,真有些使人不忍心断了它们的舔犊之情。那景那情,使我“非狠狠揍它一顿”的火气顿时烟消云散。我轻轻地牵着牛绳,让它多享受一份慈祥的母爱。十天半月,它逐渐安定下来,它似乎知道孙悟空的跟头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,认识到这里是它的家,在家里应该好好地休息和安静地睡觉。
它应该学本领了,就像我每天要上学一样。到了田头,它不认识犁路,横冲直撞,犁头插进土层,它负不了重,直往后退。大伯是“牛师”,说它颈粗肩宽,后腿粗壮有力,将来一定是一头会耕田的好牛。小牛好像能听懂大伯的称赞,很听大伯的话。短短二十来天,就学会了耕田的基本要领和懂得常用的指令。
春耕生产开始的第一天,它就“走马上任”了。我放学回来,看它低着头,用劲朝前拉犁,拉得直喘粗气,我真有点想帮它拉一把的想法。
第二天的情景,使我心痛万分。中午,我带着牛吃的粽子(稻草内裹了懒汉豆)去给它送中午饭,当大伯要卸下牛轭时,我看呆了,牛轭几乎粘在牛的肩膀上,颈肩牛轭处血肉模糊,牛轭上血迹斑斑。“它还是孩子!”我埋怨着大伯。大伯有大伯的道理,春耕生产是耽误不得的,不把田犁好秧苗怎么插得下去呢?大伯只能任凭我的埋怨。下午,我可爱的小牛,当牛轭再次套上肩头,它像没事一样,照耕不误。我回去拿了一件爸爸的旧衣服给它套在肩膀上,把牛轭用旧布包得软软的,这样,我心里才觉得宽舒些。直到春耕生产结束,它的肩膀上才结下了一层厚厚的痂。
第二年,它又长出了两颗门牙,和原来雪白的四颗牙齿排列得整整齐齐,更加逗人喜爱。这两颗牙齿的长出,说明了它已到了青春期,它的力气也更大了,拉一张犁轻轻松松,别的牛一天只耕一亩地,它一天两亩早就耕好了。到了夏收夏种,天气十分炎热,只要肩上套上犁杖,就连牛毛也湿淋淋的,它却有一股使不完的劲。
当时,我们生产队有三头牛。如果农耕只需用一头牛,那就非它莫属;如果要用两头牛,它必定是其中之一;如果三头牛都要用,它绝对不会缺席。“有一份力,就耕一份地。”这样的好牛,谁不喜欢呢?
以后,我升入了初中,住到学校里去了,才把放牛绳恋恋不舍地移交给了我的弟弟。
岁月沧桑,从我放牛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,农田耕作依靠牛的现象早已被拖拉机替代了。但是,每当我回到家乡,来到曾经被牛耕作过的田野上,行走在牛曾经走过的阡陌间,我放过的那头小牛,会飘飘然地来到我的身边,用头从下向上往我身上撞个不停,像按摩似的,撞得我心里甜甜的、痒痒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