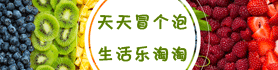凉意萧萧的秋日早上,我又回到故乡。母亲在时,此刻她一定坐在门前,晒着太阳择着菜。而今柴门依旧,母亲却已走了11年了,今年也已一百岁了。
难忘2000年元旦,早晨起来,阳光灿烂,气候温和,寒冬里碰上一个好天气,心情格外好。下午三时,电话响了,弟媳妇说母亲去世了。我一下惊得叫了起来:“你说什么?”……
就在前一天上午,我和爱人从金华去江山看望母亲。我刚跨进门槛要叫一声“娘”,不知母亲已听出我的脚步声了还是先认出是我了,站起来迎着我说:“你回来了”,转头又到东门呼叫在水塘里洗衣的弟媳回来做饭,一会儿又坐到灶堂里烧火,红晃晃的火光映照着母亲黄色的脸,明亮的笑容磨平了她脸上的皱纹。我斜对着母亲坐着,心里想,母亲的思维像程序未乱的电脑,还正常,行动还能自管自,又没什么大病恶病,体检指标都正常,心态也好,无烦无恼,一定能多活几岁,活到一百岁。
中午吃饭,母亲一如以前当家招待来客一样,时不时筷指好菜,叫我们“吃啊,吃啊”。母亲的叫唤带来一股暖暖的家庭气息。家有老人真好啊!儿子再大也是小孩。因为母亲,我对故土留下了缠绵悠长的乡思。
而现在,仅仅一天,母亲怎么突然走了呢?我又在傍晚回到了母亲身边。
母亲静静地躺在已掀了被褥的木板床上,四周空空,显得格外瘦小,一张薄薄的盖面纸,把我们隔开阴阳两个世界。我慢慢抚摸母亲的手,又冷又软。我轻轻呼唤母亲,母亲再也不能回应了。敬爱的母亲就这样无疾而终,不辞而别了。
而逝去的原因竟是那么简单:母亲喜欢吃饼干,昨天我给她捎来些饼干。今天下午弟弟一家见天气晴好,都去地里干活了。母亲自己摸了些饼干吃,可能吃的时间长,没有喝水,噎住了。如果当时身旁有人,一口水一冲就过来了,可惜旁无一人。
我站在母亲面前,泪如泉涌。许多往事像车道两旁的树木一样一道道闪过:我刚会走路,母亲牵着我,到门前的须江边上洗衣服,母亲光脚站在水里,高举着棒槌“啪啪”地槌着鹅卵石上的床单、衣物,我在岸上看着眼前小鱼儿追逐,江中心一条条挂着白帆的船儿轻轻掠过;读书上学了,晚上在昏黄的油灯下,母亲纳着鞋底,我做着作业;到中学了,冰天雪地,我还穿着两条单裤,母亲狠了狠心,卖掉娘家陪嫁来的一对烛台,为我裁了条棉裤;困难时期过年,猪肉珍贵,母亲自己不吃,坐在桌旁笑盈盈地看着我们兄弟一块块往自己碗里拖;1964年我高中毕业,因生病发烧高考不第,第二年想去再考,我写了报名申请去大队里盖个章,管章的人没给盖,从不求人的母亲接过我的申请,疾疾地找去还是不成,回家后母亲坐在床沿上,眼泪“啪嗒啪嗒”地流了出来。……母亲是我的生命之源,也是我情感的根据地,我灵魂中那些最原始、最真挚、最亲昵的感情首先来源于母亲。这些年条件好了,我一直盘算着如何孝敬母亲,我曾动员她住到我家里,曾打算陪她坐一回飞机,上一趟北京,去一次成都见见她一别五十年未晤的妹妹。一条都没来得及兑现,母亲就永别了。
母亲大半生都是在穷困中度过的,一辈子有如冬天里迎着北风赶路,遇到许多艰辛和磨难。我思念母亲,首先是因为她的苦难。
1942年5月,日本鬼子从衢州进犯江山。听到由远而近的枪炮声,乡亲们你传我,我传你,各奔东西逃难了。我的父亲和叔父挑了两担大米、衣服、锅碗等家杂,带着我母亲、婶婶和我的哥哥,两个姐姐往东逃,约莫逃了五十里,落脚到了一个叫下西畈的深山老林里。父亲担心东西不够,当晚又和叔父折回家,准备再挑些吃的用的来。不料第二天门前的须江发了大水,过不了江,下午鬼子已逼近村北头的火车站,父亲和叔父只得当晚趁着夜色携着奶奶往西逃去。母亲这边等啊等,从早望到晚,一天、两天,不见父亲的踪影,又听当地人说这山林里土匪多。母亲有了一种不祥之感,她脱下小女儿脚上的布鞋,撕开鞋心里的两层布,掏出衣袋里的钱压进去又缝上。果真,两天后的下午,一伙匪徒举着枪,挥着大刀窜来了,匪徒们抢走大米、衣服、蔬菜,又叫着要钱,母亲苦苦哀求,说男人们还没回来,实在没钱。匪徒们不信又搜身,没搜到,临走把灶头的一罐猪油也挟走了。
本来逃难至此,住的是山林草棚,没有什么财物,经此一劫,彻底地一无所有了。没有房,没有粮,没有菜,没有换洗衣服,没有支撑一家人活下去的男主人。母亲和婶婶愣愣地你望我,我望你,只觉两眼发黑,天昏地暗,抱着三个小孩子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。
太阳落山了,夜色从四面八方合拢过来,整条山谷里黑黢黢的,显得格外的阴森恐怖。草棚又没有门,只几棵树枝挡着。山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,母亲以为土匪又来了,整夜搂着孩子不敢睡觉。天亮后,看着两顿没吃的孩子饿得又哭又叫,母亲流着泪想,再苦也不能这样等着死啊?她从小女儿的鞋子里撕出那几个钱,嘱咐了孩子一番,带着婶婶冒险摸出山林。远远地,看到炊烟飘荡,走到跟前是个小村子,东看西问,哪家都没白米要卖,只有一家有些焦米。焦就焦吧,救命要紧,妯娌两个买了袋焦米回来。有了焦米,一家五口人的命暂时可以吊住了,但在这荒无人烟的山林里,最可怕的是土匪、野兽、毒蛇,哪一样都可以瞬间收拾你。无比的担心和恐怖像千斤重石一样压在母亲心里,母亲又生性老实,哪里受得了这份压力,经得住这种惊吓?几天后,母亲发了虐疾,高烧不退,山林里又找不到土医,撮不到药。那焦米又是房子被烧后幸留下来的糙米,因过了一遍火了,煮不烂,粘不起,做出的米粥一锅黑,一片焦味,吃后气大胀肚,又天天没有油没有菜,母亲病得越来越重了,几次昏死过去。母亲自感这命没望了,对婶婶说:“二婶,我不行了,你们另逃地方吧,孩子托付给你了!”婶婶哭着说:“要死一起死,要逃一起逃,刀劈下来也丢不了你!”没有药,没有医,就靠一家人的温暖,也算穷人命大,这地狱般的日子熬了一个月,母亲的高烧退了,身体慢慢好转起来。几天后,因江西战事紧急,日本鬼子撤离江山,往上饶方向集拢了。
多年后,许多苦难都在母亲心里消化了,唯有这一遭遇,母亲一直忘却不了,就像个影子,长长地投射在她的心里。少年时我听她谈起是听故事,长大后听了则有说不尽的沧桑和感慨:这样的大苦大难真是难为羸弱的母亲,也是实实在在的家仇国恨啊!因之我更加理解和敬重母亲。
母亲还遇到一次危险,那是1971年夏天,母亲去捞猪草。一个长长的清清的湖塘里,水面下飘着尺把长的像麦苗叶子一样的水草,又嫩又鲜,是猪的美食。母亲先是在湖边抓,慢慢手随草去,由边向里,不料湖底又滑又陡,脚下一溜,母亲滑出去了,水一下漫到胸前,母亲急得叫了起来,正好城里下放到本村的一个姑娘路过,这姑娘蛙泳队出身,水性很好,一个猛子扎下去,把母亲拉了上来。三年后这姑娘成了我的爱人,她和我提起这事,我问母亲,母亲说:“这真是天意!但和逃日本人那次完全不一样,这回没有枪逼,没有刀吓,又无牵无挂,我没怕。”
母亲活了88岁,至少有四分之三的年轮是在为温饱拼博却难及温饱。现在餐桌上丰富寻常甚至有人不屑一顾的米饭、面食,在母亲那代人是最珍贵的东西,是终生起早贪黑奋斗却始终达不到宽余的东西。母亲一生操碎心的就是一家人的糊口,她当家持家时,平时算着吃,一点不敢放手,一年中有半年早晚吃的是番薯等杂粮,到了农历三月进入春荒,常是菜粥菜饭,有几年菜粥也断了,就荸荠当饭,荸荠再没了,就上山挖土茯苓根充饥。那时食用油更是稀缺,我多次看到母亲一篮青菜洗好切好了,锅也热了,就是没有油,没油菜就粘锅,炒不起来。母亲只好找来蜡烛,在滚烫的锅里快快地磨两圈——光光锅,然后倒下青菜。我在家时喜欢抓鱼,那时鱼又多,门前须江里别人炸鱼时跳下去拾两条;洪水退时拦几网;屋后渠里沟里选一段,两头作个坝,抓起脸盆哗哗地把水打干,都可以逮到不少鱼。我兴冲冲地提鱼回来,母亲却愁了眉,她说:“碰到鱼腥,打破饭甑”,鱼好吃下饭,大米却要多费了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后,粮食足了,鱼肉多了,生活好了,母亲过上了再也不愁温饱的日子,可这时母亲年纪也大了,又苦惯了,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低了,花钱的地方不多了,有钱也不会花了。许多终生追求的东西,已隔岸看花,风淡云清。那些年儿女们给她的钱,她走后都在枕头底下压着。有时难得带她到餐馆吃顿饭,她也不情愿去。她说:“享福也要年龄啊,还是让我自在点好。”再丰盛的宴席她都感到陪着坐着是受罪。我家里条件好一些,我一度让她住在我这边,可她住了十天半月,就吵着要回去,她说她喜欢开窗就见山水,出门就是田野,碰见就是熟人的老家。
母亲和许多同代人一样,一辈子思想没有开放过,个性没有舒展过,压制着自己的天性过日子,从来没什么奢望。习惯了一辈子忙碌,一辈子担当全家人的吃穿洗补,一辈子操心着全家的喜怒哀乐,从出嫁到老去,从年头到年尾,从日起到日落,早晨我们还在酣睡,她先起来做饭,白天我们出去了,她浆洗衣服,摘菜洗菜,收拾卫生,喂猪饲鸡,晚上我们睡了,她挑灯缝补。在忙忙碌碌中,在平平淡淡中,在默默无闻中,岁月就这样跚跚地走来,又悄悄地逝去,母亲就这样由青春靓丽到皱纹纵横,老态龙钟。
母亲终生把自己摆在服务的位置上,以罕见的无私和真诚关爱照顾家人。母亲做了一辈子饭,却从来没有先吃饭,饭做好了,男人不上桌她就不吃。等大家都坐下吃了,她才上桌。有点好菜剩下,她也不吃,她筷子头给它撇撇整齐,伸个指头将沾到菜碗外沿的汤一搅,又端起放到菜橱里,她说留给做功夫的人下顿吃。我们兄弟长身体时,每年春天到了,母亲都要给父亲和我们每人炖只鸡补补,唯独她没有,她说“我没下地就不要了”。粮食紧张时期,吃饭困难,父亲朋友又多,有时刚端上饭菜,客人一脚踏进来了,家人中不免脸有难色,母亲见状总是说进门就是客,一边说一边盛好饭端到客人面前。
世间万物都有自身的平衡。母亲一生付出很多,可得到却很少。她的一生是倾斜的。母亲平生最怕麻烦人,最怕无功受报,邻居尊重她,杀猪给她端碗吃的,做寿给她一双寿桃,她心里就很不安。对自己的子女,她也从不讲困难,不提要求,总是说她一切都好,你们自己照顾好自己。有些事正因为她自己从来不说,以至于我们忽略了她的需要,淡忘了她在悄悄老去。反过来,为家人,为子女,她想的很细,做得坚决。一天,家中一间厢房里的灯泡坏了,嫂子去换只灯泡,厢房前有走廊,后边紧挨邻居房子,白天和晚上一样黑,嫂子没留心,卸了旧灯泡后,一个手指触到了灯头里头,一下触电了,“嘭”一声倒在地上,灯头仍粘在她手指上,正在隔壁的母亲听到响声,急忙跑过来,朦朦胧胧亮光中见嫂子倒在那里。这时门外正有年轻人在谈天,但母亲觉得叫他们来不及了,自己冲上去抓起灯线就甩,头一下一只手抓的,没有抓断,母亲又两只手抓住灯线,用尽力气猛然一拉,灯头从嫂子的手里拉出来了。母亲又去抱嫂子,嫂子昏过去了。母亲哭着冲到外面叫救命,正好碰到村前的水文站里的一个技师,在他的指导下做人工呼吸,半小时后嫂子醒过来了。母亲一生身体不错,直到去世前都正常。村中老人、街坊邻居羡慕她,恭贺她长寿,可她总是说:“可以走了,不能再活了,活下去拖累子女了。”母亲说的不是客套话,也不是没有愿望和力量生活下去,而是真的怕给子女添麻烦。母亲为子女想得太多了!
母亲没有文化,没有专长,更没有经济实力,对我们兄妹非常关爱,但条件所限,只能给我们最基本最勉强的吃穿,我们的成长和那个时候的多数小孩一样,是像路旁的野花一样自然长大的,那时社会上也没什么学前班、辅导班、培训班,即使有了我们也没钱去上。年轻时对这些想得不深,长大了自己为人父母了,我才悟到,其实母亲也给了我们很好的教育培养,那就是她勤劳朴实,干干净净为人为事的榜样。母亲终生深受佛教的影响,敬畏天地,深信因果,向善拒恶。不会说假话,不敢做坏事,待人以诚,吃得起亏,安贫乐道,自甘寂寞。一辈子没有和邻居拌过嘴,没有和家人红过脸。婆媳之间,妯娌之间,历来较难相处,利益、老人、小孩,言高语低,马勺碰锅沿,很容易擦出火花,母亲却一生和婆媳、妯娌处得母女一样,姐妹一样。母亲是大媳长嫂,但意气上从不争高低,乐于当助手下手。平时做个豆腐,石膏点得够不够,她要叫二婶看一看;重阳节蒸个焙糕,米浆发酵得行不行,要叫二婶定一定。从我记事起,就见母亲的头型是在脑后挽个发髻,穿的都是士林蓝或青色的、胳肢窝下结扣的大襟布衫,一身旧式农村妇女最普通的装束。母亲像儿子信仰她一样信仰那些善良美好的东西。小时她常提醒警示我们的就是要学好,不允许我们和德行欠缺、手脚不净的小孩交往结伴,她说:“跟着好人学好人,跟着巫婆下神神。”对我们学习成绩好差她不过问,德行上有没有犯错却很在意。那时候,孩子如果拿人家一件东西,或说一次假话,打一次架,母亲是很上心,很觉抬不起头的。我小学五年级时,为上渡船的先后,和本村的几个同学与邻村的几个学生打起了架。傍晚放学时,班主任老师随我一起到了家里,和母亲说了打架的事,从来没有对孩子动火的母亲这次很生气了,待老师一走,拿起还留着枝叶的一枝毛竹条子朝我脚上扫了过来。母亲说:“早点迟点都能过河,你为什么还打架欺负人?”母亲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对我动过手,可因为她自己做得好,让我铭刻在心,终生受益。
母亲是个极平常的人,一辈子平平淡淡,没有功业,没有财产,没有名声,也没有享受。今天,当她早已化为泥土,当我也一天天老去,对人生,对世事洞察加深的时候,却感到这平常老人身上有些东西也像这秋夜一样静美。